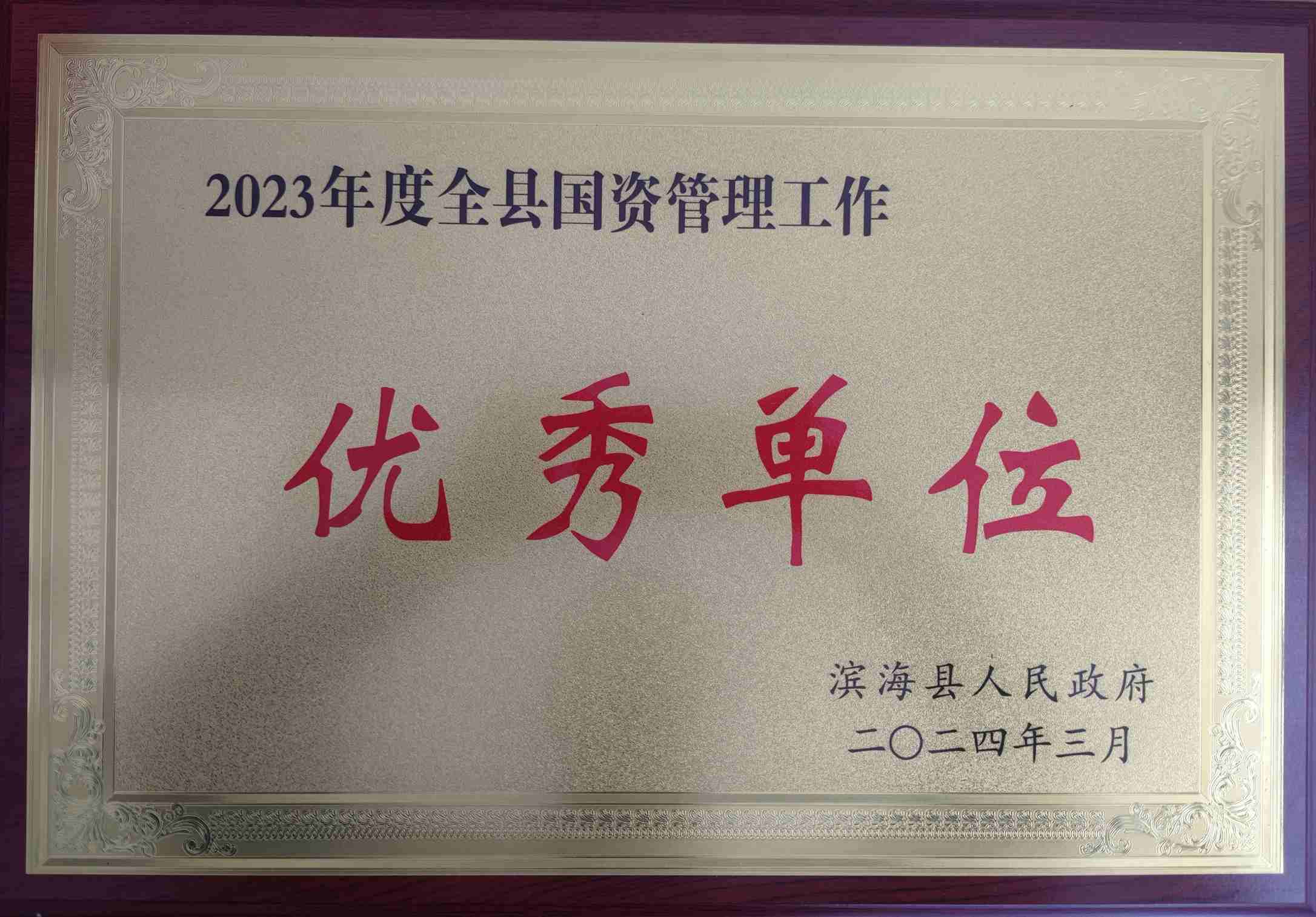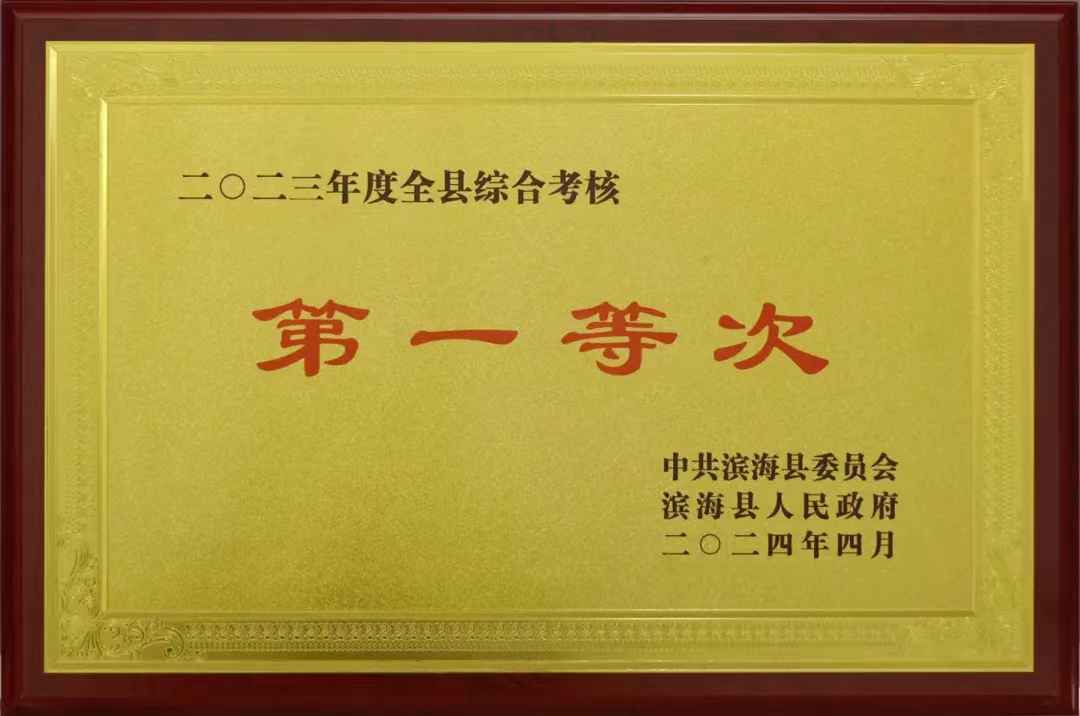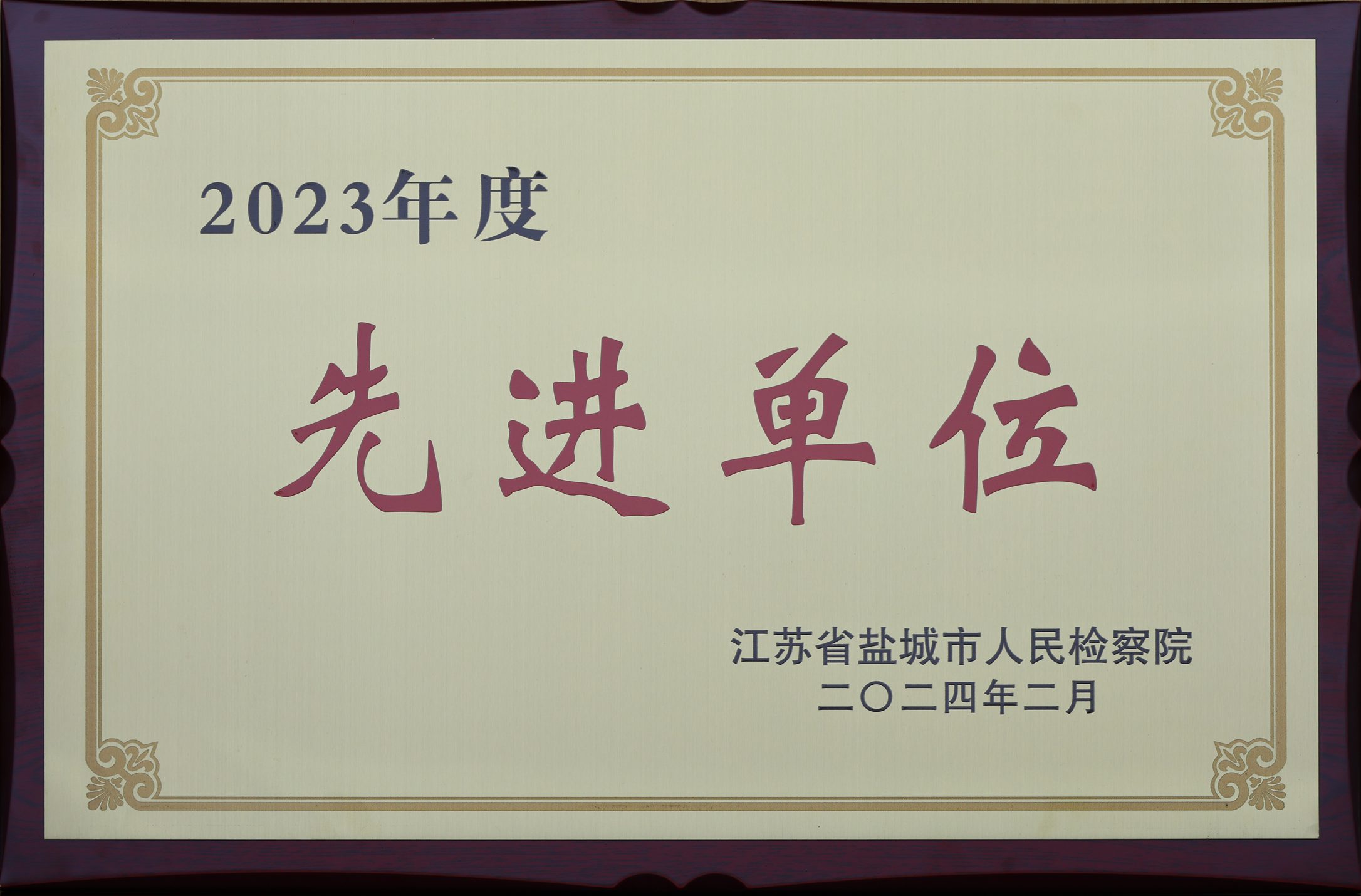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殴打伤害无辜、肆意挑衅、横行霸道、毁坏财物、破坏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293条对该罪名作了相关规定,2013年7月15日施行的《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又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近年来,寻衅滋事类案件高发,严重影响和社会秩序,制约了经济发展,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从分析安徽省凤阳县检察院从2011年以来办理审结的寻衅滋事类案件基本情况入手,总结其,从具体数据中分析凤阳县该类案件近年来高发的原因,进而探析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以期能够成为后事之师。
一、近四年凤阳县检察院办理寻衅滋事类案件的基本情况
自2011年以来,凤阳县检察院共办理涉嫌寻衅滋事罪案件76件181人,其中2011年24件67人、2012年22件33人、2013年19件47人、2014年截至10月11件34人。案件数量占当年总案件数的相当大的比例,且涉案人数众多,多为群体性的事件而社会影响恶劣,案件伴随着信访危机。
二、该类案件呈现出来的特点
从这四年办理的案件来看,呈现出显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犯罪嫌疑人性别来看,男性居多
共181名犯罪嫌疑人,男性176人,女性只有5人(其中2012年1人、2013年2人、2014年2人),男性占了约97%,女性只占了3%。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客观方面决定了其犯罪主体主要是男性,根据《解释》所规定的行为分别是,殴打、辱骂、恐吓,或毁损,占用他人财物;追逐、拦截;强拿硬要,毁损财物;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可以看出犯罪行为方式偏向于暴力,男性趋向于暴力犯罪这一观点在德国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一书中,就犯罪的性别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的研究。
(二)从犯罪嫌疑人年龄来看,青年人居多
综合四年数据,以20岁以下,30岁以下,40岁以下,40岁以上四个年龄段来看:20岁以下的犯罪嫌疑人共77人,占总数的42.5%;30岁以下的68人,占37.6%;40岁以下的19人,占10.5%;40岁以上的犯罪嫌疑人15人,仅占9.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30岁以下的犯罪嫌疑人占了80.1%,主要是青年人居多。
(三)从犯罪嫌疑人身份来看,农民、无业居多
181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农民67人,占了37.2%,无业100人,占了55.2%,共167人,占了全部犯罪嫌疑人的92.3%;其他身份包括个体、工人、学生等仅有14人,占7.7%。无业人员占了大多数由于他们没有正当职业、无所事事而惹是生非;加之犯罪地点多集中在饭店、KTV等娱乐场所,这些地方人流集中,且发生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彼此矛盾摩擦纠纷易起。
(四)从犯罪嫌疑人受教育状况来看,学历偏低

从上图表可以看出,181名犯罪嫌疑人初中、小学及文盲共学历167人,占92.3%,犯罪嫌疑人学历普遍偏低,受教育水平不高决定了其法律意识淡薄,遇事不知道寻求法律解决途径而是用拳头说话、争强斗狠。
(五)发生地点多为矿山和饭店、KTV等公共消费和娱乐场所
分析这些案件,80%以上发生在饭店、KTV等人流聚集的公共消费和娱乐场所,一部分发生在矿山等地,且伴随着聚众斗殴行为。
三、寻衅滋事犯罪高发的原因
寻衅滋事类犯罪案件近年来持续高发,既有社会发展转型期矛盾激化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本地小环境的特点,无论是从近四年我院办理的该类型案件数据分析还是从具体案件入手,对该类案件高发之原因进行探析都是有章可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矿产利益引发矛盾
凤阳县盛产石英砂,矿区成为利益集中地,利益驱使下各种争斗不断,且多伴随涉黑、聚众斗殴等犯罪,例如,两家为了争夺塘口,一家组织社会上闲散人员到另一方闹事,另一方如果有人受伤,很可能集结多人进行报复性打击常常导致几百人一起混战多人受伤。
(二)酒风盛行,酗酒滋事
从凤阳县检察院办理的具体案件来看,很多寻衅滋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在饮酒后进行犯罪的,有人形容饮酒与犯罪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往往清醒时不敢不会做的事情,在酒精的刺激下却去做,这种效果对于男性而言更明显。饮酒与该类案件的关系,从案件的发生地点大都是饭店可见端倪。
(三)犯罪嫌疑人个人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
从犯罪嫌疑人个人素质来说,大多数都是30岁左右的无业或者农民青年,该群体年轻气盛容易意气用事,自控力差,文化水平不高,当其处于无所事事且饮酒的状态下,一旦遇到一点小摩擦就会极易造成情绪的宣泄口。很多十几岁的犯罪嫌疑人是离开农村寄居城市的流动人口,缺乏父母的监管,没有正当职业和经济来源,混迹于网吧、酒吧、浴场、矿山等场所,充当“打手”收入为生。此外,这些青少年大都沉迷于网络游戏,思想受到暴力因素的影响,对于江湖义气的信仰多于法律,对于别人的生命健康不以为然而经常为了点小事大打出手。
(四)寻衅滋事罪罪名本身的原因
寻衅滋事罪从原来的流氓罪分离出来,流氓罪原来被称为口袋罪,而寻衅滋事罪被有些学者形象的称为“小口袋罪”,所谓“口袋罪”就是找不到合适罪名定罪时找一个相似的罪名,刑法中有很多这样的罪名,寻衅滋事罪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寻衅滋事罪不断攀升,很多侦查机关移送报捕、审查起诉的罪名一旦找不到合适的罪名时,都以该罪名进行报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使得该罪名变成“口袋罪”。例如,这样一起案件:王某、李某骑电瓶车与对面也骑电瓶车的张某、陈某(二人是协警)相撞,导致李某头部受伤,王某与与张某、陈某商议打120将李某送去医院进行治疗,但张某打电话叫来了同是协警的孟某到现场,孟某、张某、陈某与王某、李某商议过程中发生纠纷,对二人进行殴打,造成王某轻微伤、李某轻伤。该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孟某行为定性时存在问题:一是如果定故意伤害罪要求必须造成轻伤,但是被害人王某只是轻微伤,而被害人李某的轻伤现有证据无法区分其伤情是之前的交通肇事造成的还是被殴打所致;二是该案从视听资料上看到犯罪嫌疑人孟某在被害人不断躲避逃跑求饶的情况下,气焰嚣张、一直追打被害人,性质非常恶劣,且其身为辅警,若不对其定罪处罚,可能造成“不足以平民愤”的社会影响。
故意伤害罪条件不够,办案人员只能往相似的上面靠,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或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本案中,孟某的行为符合该条规定。
实践中,类似该案件的情况很多,也是寻衅滋事类案件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五)执法力度不够
寻衅滋事犯罪案件多发生后,多数以调解结案,当然这对快速化解社会矛盾有很大好处,但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为了快速化解法律惩处危机,选择“花钱买平安”,但是这并不代表双方的矛盾真正化解,经常出现第二次纠纷的行为。办案部门为了快速走完案件的法律程序存在超范围调解和降格处理,这间接纵容了该类犯罪行为,导致有些人认为打人没什么人,主要花点钱就可以解决的错误心态。
四、预防和减少寻衅滋事犯罪案件高发的对策
寻衅滋事案件高发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群众安全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来防对:
(一)加强社会面巡逻防范,且要积极履行职责
寻衅滋事案件具有突发性、暴力性和反复性且发生在公共场所,如果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是可以避免的,这样既能够从开端遏制犯罪,也能够节约司法资源。然而,在办案过程中有些案件的视听资料可以看到,巡警明明已经到了矛盾现场,却没有积极采取制止措施而是站在一旁观看,对于一触即发的争斗不闻不问,漠视整个犯罪行为的发生,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执法部门加强对辖区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巡查控制,及时发现调处矛盾纠纷,主动盘查检查可疑人员,依法严肃查处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行为,最大限度地压降案件高发势头。
此外,对接报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警情,要迅速集中优势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控制局势和涉案人员,认真开展调查取证。
(二)要坚持用足法律武器,打防结合
在办理此类案件中要坚持依法严格处理,坚决防止超范围调解和降格处理。凡嫌疑有据能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够治安拘留的违法犯罪人员都要给予打击,绝不让其形成气候;对涉案在逃的嫌疑人员,要严格落实破案追逃责任,尽全力进行追捕,坚持扫除犯罪人员的侥幸心理,绝不给犯罪人员留有逃避打击的空间。积极预防和严格打击处理相结合,惩处犯罪也是预防的一种,特殊预防。
(三)切实加大法制宣传工作力度,增强法律意识
要坚持传统宣传与现代传媒相结合,普遍宣传与重点人群教育相结合的手段和方式,切实加大法制宣传工作力度,大力提高群众的守法意识,引导其采用正确方法,合理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尤其是针对高发区、高发人群,利用各种宣传活动进行普法教育,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对于法律常怀敬畏之心,遇事冷静,促进其从不敢犯法到不愿犯法意识的转变,从而做到清本溯源。
(四)杜绝将寻衅滋事罪故意作为伤害罪的兜底条款
寻衅滋事罪作为情节犯,只要“情节恶劣”就构罪,《解释》对“情节恶劣”进行限制,其中一款规定是“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定罪时要求造成轻伤或者轻伤以上的结果。当一个有两名案件的被害人的伤情都不构成轻伤时,但是该案件由的确性质非常恶劣造成很大社会影响,这时候寻衅滋事罪便成为一个堵截性罪名。例如上文提到的孟某涉嫌寻衅滋事案,之所以认定孟某构成寻衅滋事罪而非故意伤害罪,是因为一名被害人只是轻微伤,另一名被害人虽然轻伤但是却不能认定是孟某殴打所致。再如,引起广泛关注的肖传国雇凶伤害方舟子、方玄昌的案例,为打击报复,用辣椒水、锤子伤人的行为,性质恶劣,但是只造成了轻微伤,不定罪又不足以平息舆论,所以司法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定罪,但是无论从肖传国古雇人伤害的主观意图,还是客观行为,都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因为结果是轻微伤,所以用寻衅滋事罪来兜底。虽然《解释》限定了“情节恶劣”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办案人员应该严格依法办案,不能将寻衅滋事罪变成故意伤害罪或者其他罪名的兜底罪名。
(作者系安徽凤阳县检察院检察长 张平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