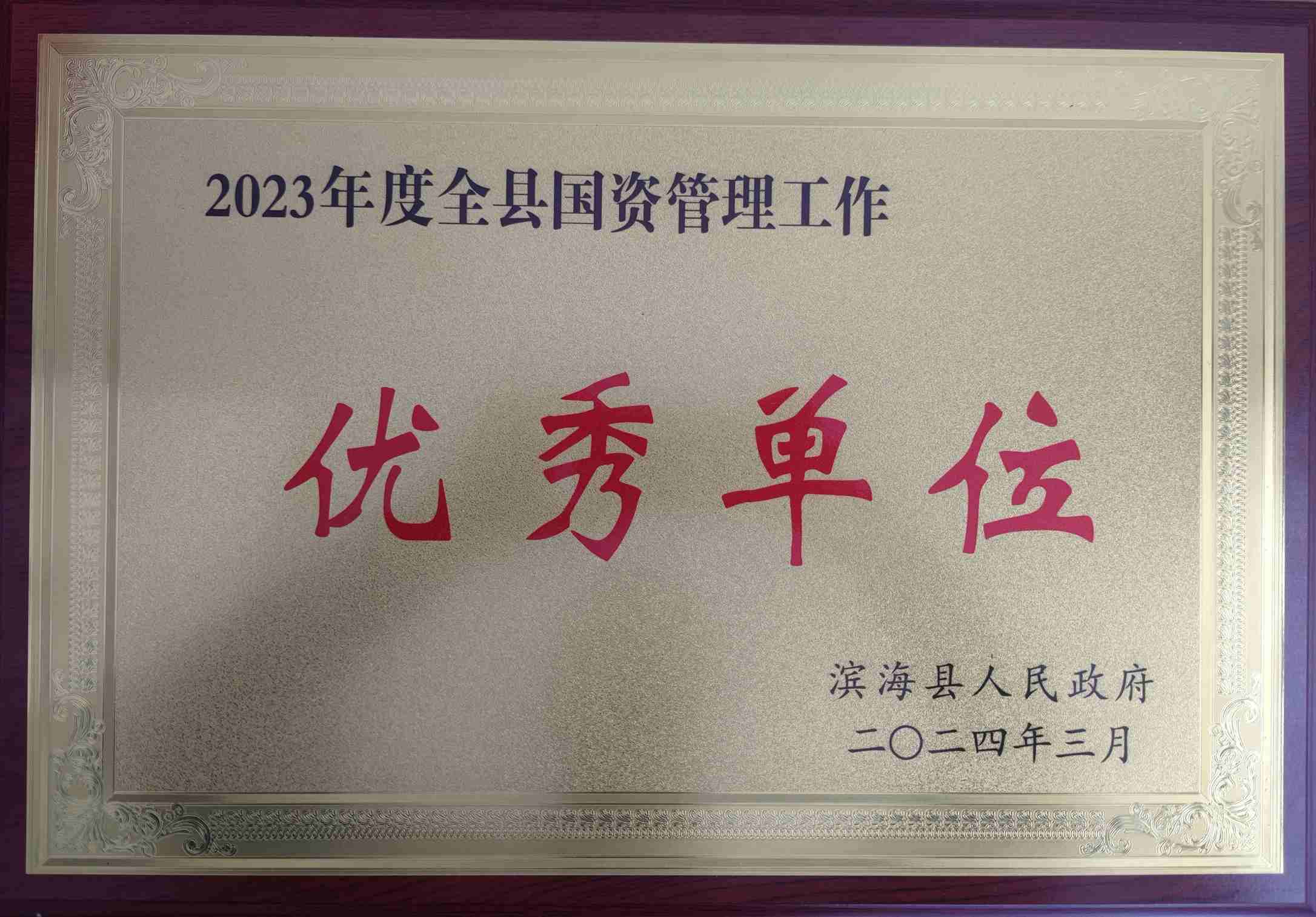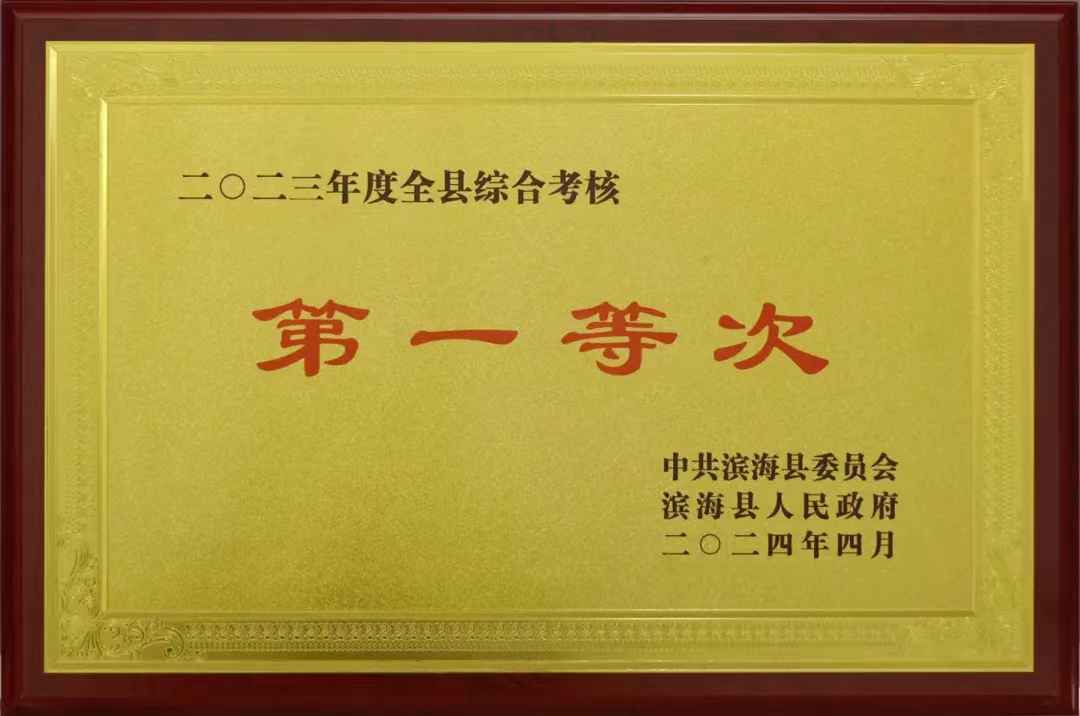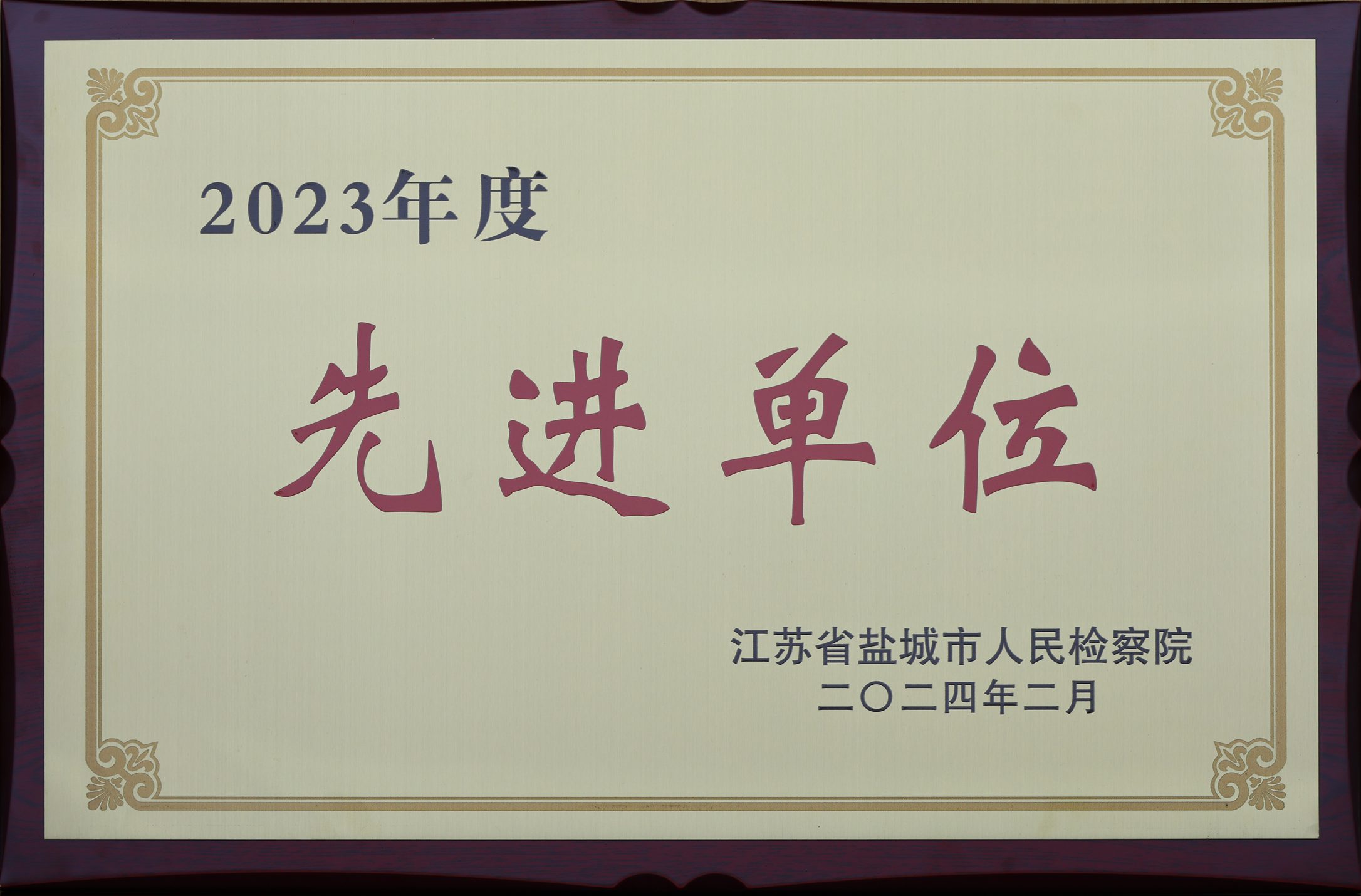文章摘要:对刑法个罪犯罪类型的界定,是进行刑法个罪研究和实践的基点。自从醉酒驾驶以危险驾驶罪之名入刑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犯罪类型一直存有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抽象危险犯和行为犯的争论。当前,理论界大都对其以抽象危险犯的构成来研究,而实务界大都对其以行为犯的标准来操作。本文中,笔者追本溯源,从刑法理论上对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关系再次加以比较和厘定,进最终将醉酒驾驶的犯罪类型界定为抽象危险犯,而非行为犯。
关键词:醉酒驾驶 危险犯 抽象危险犯 行为犯
对于醉酒驾驶究竟是行为犯还是抽象危险犯,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认为,醉酒驾驶是危险犯,而且是抽象危险犯; 有人认为醉酒驾驶既是行为犯,也是危险犯; 还有人认为,醉酒驾驶只是行为犯,不是危险犯。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分歧,根本原因是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对行为犯与危险犯的关系问题纠缠不清,却莫衷一是。笔者欲在厘清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对醉酒驾驶的犯罪类型做出较为中肯的界定。
一、危险犯与行为犯关系之厘定关于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关系,学界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危险犯属于行为犯的一种。理由是危险犯只须实施一定行为,而不需要发生一定的实害结果,这一点完全符合行为犯的本质,因而可以纳入其中。 二是,危险犯属于结果犯的一种,与行为犯相对应。理由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中的“结果”既包括物质上的结果,也包括非物质上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危险犯构成要件要素之一的某种危险状态也是结果,所以危险犯包含于结果犯的范畴之内。 三是,危险犯是一种独立的犯罪类型,既不同于行为犯,也不同于结果犯。理由是一方面,从犯罪的发展过程看,相对于行为犯,危险犯离危害结果又更近了一步,其危害程度高于行为犯;另一方面,危险犯只是造成某种危险,还未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当然不是结果犯。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有以下看法:
(一)危险犯与行为犯并非同一逻辑层面的概念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危险犯与行为犯并非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讨论的概念。 1、危险犯对应于侵害犯危险犯是与侵害犯(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其区分的逻辑起点是“行为构成中的行为客体是受到损害或者是在整体上有危险性”。 如果行为对于客体造成了客观有形、外在可见的损害,就是侵害犯;如果行为对于客体仅仅造成的是某种或轻或重、抽象无形的危险或威胁,则是危险犯。根据危险程度的不同,危险犯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 笔者认为:具体危险犯是指,以一定危险状态作为与行为并列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危险犯。这类危险犯往往在法条中明确表述要求发生某种危险状态,即以某种危险状态作为由行为产生的客观结果,从而成为与行为并列的构成要件要素,缺少这种作为结果的危险状态,该危险犯就不能成立。抽象危险犯是指,只以遂行某种具有法益侵害危险性的行为为其构成要件要素,而不要求发生某种危险状态的危险犯。这种危险犯的成立,并不需要在个案中出现由行为引发的某种实际危险状态的结果,只要行为人实行了在刑法评价上具有某种危险性的特定举止行为就足矣。“防止具体的危险和侵害,仅仅是立法的动机,而不是使这种具体的危险和侵害的存在成为行为构成的条件。” 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一般是具有法律拟制性的危险, 即作为其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一经做出,在规范评价意义上就直接推定其具有危险性,而无须考察其是否造成实在的危险状态。应该说,是否以一定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其构成要件要素,是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明显界限。 2、行为犯对应于结果犯行为犯(形式犯)是与结果犯(实质犯)相对应的概念,其区分的逻辑起点是: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否以发生一定结果为其必备要素。在德、日刑法理论上,一般都以“单纯活动犯罪”(德)或 “单纯行为犯”(日)来指称我国刑法上的行为犯,“单纯”一词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此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犯罪构成所要求的特定行为,就构成犯罪,不须伴有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危险。由于危险犯与行为犯并不是在同一逻辑层次上进行的罪质形态分类,因而两者之间很难划出明显的界限,难免出现内涵外延上的交叉重合,但又并非完全重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危险犯与行为犯是基于不同区分标准形成的概念,既不能将危险犯与行为犯划等号,也不能将其与结果犯划等号。
(二)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内涵外延形式上有交叉通过以上对危险犯和行为犯内涵的界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具体危险犯除行为外,还要求以一定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其构成要件要素,而这种危险状态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结果,因而其属于结果犯范畴,与行为犯有明显界限,这一点在学界并无争议。目前比较模糊的是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关系。笔者认为,单从形式的构成要件来看,抽象危险犯应属于行为犯范畴。理由是,从构成要件的形式来看,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只须遂行被刑法拟制为具有特定危险性的行为就可以了,这与行为犯的构成要件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因而其可以归于行为犯之中。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并不赞成将危险犯单纯地归入结果犯,或单纯地归入行为犯的做法。从形式的构成要件角度出发,应该有区分地将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犯归入结果犯范畴,将其中的抽象危险犯归入行为犯范畴。这与“危险犯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 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谋而合的。
(三)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内涵外延实质上有区别 如前所述,具体危险犯与行为犯有明显区别,在此无需多著笔墨,需要着重分析的是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之间的细微差别。之前虽将抽象危险犯归入行为犯范畴,但仅仅是基于形式的构成要件角度,况且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在内涵外延上并不能完全重合,这就表明两者之间还有存在差异性的空间,需要我们对其再做精细的区分。下面,笔者将从实质的刑事可罚性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从行为的自然发展来看,行为犯中的行为实施完毕,必然造成法益的实际侵害,但抽象危险犯中的行为实施完毕,却并不必然造成法益的实际侵害。例如,在强奸罪的基本犯(行为犯)中,如果强奸行为实施完毕,必然造成对妇女性自主权这一法益的实际侵害;而在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罪(抽象危险犯)中,即使盗窃或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实施完毕,最终也不一定会对公共安全这一法益造成实际侵害,而至多是一种危险。不仅如此,行为犯中行为构成的满足往往与法益的实际侵害同时发生, 例如侵入住宅以及性行为犯罪;而抽象危险犯中行为构成的满足只是与法益的危险状态同时发生。 2、基于上述分析可见,行为犯中的行为与其实际侵害结果具有等价值性,即:有行为,则必然有法益的实际侵害。因而行为犯中的行为本身就具备了无价值,这足以构成其实质可罚性的依据,刑法没有必要等到实际侵害结果出现,再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所以在客观构成要件上只须具备行为这一要素。与此相对应,抽象危险犯中的行为并不必然产生法益的实际侵害,所以该行为并不足以构成其实质可罚性的依据,还须具备法律拟制的危险状态这一条件。这一点也正是两者在反证出罪机制上差别的理论依据,即:对于抽象危险犯,完全没有危险的行为,因为丧失实质可罚性依据,所以允许反证出罪;但行为犯只要行为遂行,就具备了实质可罚性依据,因而不存在反证出罪的空间。
二、醉酒驾驶犯罪类型之界定
笔者认为,醉酒驾驶的犯罪类型应为抽象危险犯无疑。理由在于:根据前述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关系厘定,一方面,醉驾的客观构成要件在法条表述上只有“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一行为要素,而不要求出现实在危险状态这一结果要素,这一点区别于具体危险犯。另一方面,醉酒驾驶行为并不必然造成对公共安全法益的实际侵害,必须结合法律拟制的由该行为造成的特定危险状态,才足以构成其实质可罚依据,这一点区别于行为犯。而以上两点皆符合抽象危险犯的罪质形态特征。
笔者认为,醉酒驾驶的犯罪类型应为抽象危险犯无疑。理由在于:根据前述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关系厘定,一方面,醉驾的客观构成要件在法条表述上只有“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一行为要素,而不要求出现实在危险状态这一结果要素,这一点区别于具体危险犯。另一方面,醉酒驾驶行为并不必然造成对公共安全法益的实际侵害,必须结合法律拟制的由该行为造成的特定危险状态,才足以构成其实质可罚依据,这一点区别于行为犯。而以上两点皆符合抽象危险犯的罪质形态特征。
(作者系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检察院检察长)